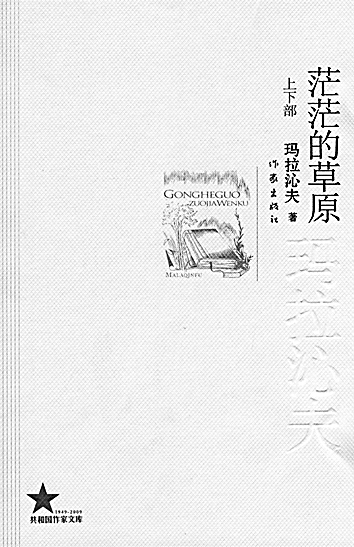

今年将迎来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85岁寿辰,同时也是他创作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65周年。随着这些重要日子的来临,玛拉沁夫也格外忙碌,《玛拉沁夫与民族文学》《玛拉沁夫与草原文学》这两本书即将出版,这些日子他正在紧张地进行书稿的最后整理。记者对玛拉沁夫的采访也是在他整理书稿间隙进行的。
1月的北京正在进入最冷的时节,大风呼啸,寒气逼人。来到玛拉沁夫的寓所,窗台上的几盆吊兰绿意盎然,旭日朝阳透过窗户洒入房间,使这一方天地显得温暖、淡定与惬意。坐在沙发上的玛拉沁夫,倚着沙发扶手侃侃而谈。眼前这位老人正在述说他八十五载的人生历程,声音嘹亮、思维敏捷,亲耳聆听仿佛能随着声调的起伏进入曾经的历史,经历过往种种的人世变迁。
文学缘:从战火中走来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是早熟型的。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艰辛和考验,又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和值得永远珍惜的回忆。回想起来,苦肯定苦,但想不起怎么苦了。革命,就得吃苦,可那些苦却那样令我们神往。或许这就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生活斗争中的价值取向,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懂得一些大道理,活得有底气。”
1930年,玛拉沁夫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现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土力根太卜村。玛拉沁夫还有两个哥哥,家境贫穷,但父母却对读书格外看重,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三个孩子有书读。为了读书,玛拉沁夫5岁时随全家搬到了母亲的娘家,那里有一所王府小学,这是附近唯一可以读书的地方。读到五年级时家中实在拿不出学费继续供他上学,玛拉沁夫只好转学去科尔沁草原的一所蒙古中学,因为那里可以免收学费。就这样,小小年纪的玛拉沁夫又一次远赴他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学校停办,玛拉沁夫只得回家去。
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在磨难与不顺中给予人一种新的希望。
玛拉沁夫辗转多日回到家中时,一支八路军部队驻守在他们村,而部队的连部恰就在他家中。当时部队战士文化水平低,一个登记战士名单的“花名册”都没有人能填写,玛拉沁夫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连长就动员他参加部队,从此,15岁的玛拉沁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部队不久,他转到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担任女政委乌兰的通讯员。那时蒙古老乡不知道政委是个什么官,只知道部队最大的官是司令,都叫乌兰政委为红司令,在蒙古语中“乌兰”是红色的意思。乌兰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去延安,现在是一支强悍蒙古骑兵部队的政委,这位女英雄在玛拉沁夫心中,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在玛拉沁夫后来创作的多部作品中,以乌兰政委为人物原型的艺术形象多次出现,比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和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的洪戈尔等。
1946年4月,乌兰送玛拉沁夫到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主要用以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当时院长是乌兰夫。安静的读书时光很快被打破,当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和平协定”,7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他离开学校再次奔赴前线,
重又回到了乌兰领导的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战区,此时玛拉沁夫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内蒙古文工团,时任团长是布赫,文工团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服从部队的统一调动。
在文工团玛拉沁夫负责写通讯报道,前线战斗中的先进典型、战斗英雄、支前模范等都是他的报道对象。此时他深感自己的汉文水平太低。玛拉沁夫接触汉文的机会不多,虽然简单的汉字还能认识,但是说熟练使用汉文写作还不行,玛拉沁夫想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汉语汉文水平。可是战事的紧张让学习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为了配合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玛拉沁夫他们奉命进行战略转移,从辽西向内蒙古北部草原撤退。那是1946年隆冬时节,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玛拉沁夫没有棉帽子,只得找来两团棉花捂住耳朵,用一块白布毛巾裹着棉花围起来,就这样艰难行军。最危险的一次,部队需要突破一个山口,必须赶在敌人封锁山口之前突围出去,否则就会有被围歼的可能。那一次玛拉沁夫背着行装随部队一夜狂奔90里路,可谓“死里逃生”。
部队撤退至内蒙古草原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来到巴林左旗林东见到了乌兰夫同志,这时条件才有改观,发了毡靴和皮帽子。1947年初,玛拉沁夫随团赶赴乌兰浩特,参与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成为我国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1948年8月14日,玛拉沁夫经布赫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东北地区战事的推进,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相继解放,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能够看的书比原来多了很多。这时玛拉沁夫如饥似渴地见书就读、有书就读、是书就读,好像走火入魔一般,夜晚吹了熄灯号之后,自己点着蜡烛能看一宿。早上只睡一小时就又出操工作。就这样,玛拉沁夫“为了学文化学了文学,又通过学文学学了文化”。“我看的书很多也很杂,耗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但是我不后悔,正因为看得多、看得杂,我的知识面较宽泛”。这段读书经历前后长达4年之久,让玛拉沁夫的汉文功底得到提高,并开始用汉文进行文学习作了。
在革命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解放战争中的玛拉沁夫就这样走了过来。“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艰险与考验,又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和值得永远珍惜的回忆。”
在战争中玛拉沁夫已经在文学创作上初显锋芒。《保卫热河》正是在热河休整的间隙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唱中朗朗上口。一部动员青年参军的短剧《参军去》创作出来就演出了,当时玛拉沁夫才16岁。
新中国成立,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949年6月,玛拉沁夫第一次来到北平,作为演出团成员参加全国文代会,在会上见到了毛主席,他们沉浸在欢乐与激动之中。
1950年,创办《内蒙古文艺》杂志,玛拉沁夫成为一名文学编辑。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火热的革命生涯为玛拉沁夫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他回忆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是早熟型的。回想起来,苦肯定苦,但想不起怎么苦了。革命,就得吃苦,可那些苦却那样令我们神往。或许这就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生活斗争中的价值取向,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懂得一些大道理,活得有底气。”
草原情:写作的永恒题材
“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写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决不称自己为作家。”
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创作灵感都来自草原,他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是写那片他所熟悉的蒙古草原。
1952年,对于玛拉沁夫而言可谓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以头条形式刊发了他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随即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在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对一个21岁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没有先例的。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于1951年,玛拉沁夫在科尔沁左中旗工作期间,临旗科尔沁右后旗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19岁的牧民妇女塔姆。她在坐月子期间遇到了一个来她家门外找水喝的陌生人,按照蒙古族传统礼节,客人不需站在门外求水,而应走进屋里喝茶,这个人的行为让塔姆心生疑虑。随后的一幕让塔姆更加认定他是个坏人,当时一阵风吹来将这个人身上披着的毯子掀起一角,突然露出了枪口。机智的塔姆设法稳住这个嫌犯,和他周旋,最后通过搏斗和别人的帮忙终于将他制服。玛拉沁夫被塔姆这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政权的忠贞、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多么可爱呀,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敢于拼命。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平平淡淡地写这个人物,而应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和整个民族新生的角度审视塔姆的事迹,表现她崭新的精神世界。”
小说创作的过程很艰辛,因为住在牧民家里,连个写字的桌子都没有,玛拉沁夫就坐着在膝盖上写作,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写了大约3个多月。玛拉沁夫心里没底,他把作品拿给同伴安柯钦夫看,问他这算不算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说:“大概算是小说吧。”虽然语气上并不十分肯定,但玛拉沁夫觉得“大概算”也就是可以了。他把小说寄给了在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
这篇小说的发表改变了这个文学青年的命运,玛拉沁夫被调到北京,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他作词的该影片插曲《敖包相会》,传唱至今。
玛拉沁夫说:“现在看我那篇小说,觉得还是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烙印:时代需要我,我顺应了时代,我也紧跟着时代长大。”
玛拉沁夫年少成名,但他心里很清楚,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自己的路还很长。他那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只写一个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和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我决不称自己为作家。”倔强的玛拉沁夫随即向组织上提出要求,他要返回内蒙古草原去深入生活。他已酝酿好写一部反映抗战胜利后内蒙古人民选择民族解放之路——即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历史性激烈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当说,玛拉沁夫参加过那场斗争的全部过程,是有生活积累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年自己只是一个小战士,对那场伟大斗争缺少宏观与战略高度的认识,再说任何作家的生活积累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作家不断深入生活、充实生活、更新生活。所以他从北京回到内蒙古后,没有在呼和浩特市停留,经组织安排径赴草原挂职深入生活去了,在明太旗一干就是三年,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
《茫茫的草原》上部以《在茫茫的草原上》书名于1957年出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但是它的下部却经过一时难以说清楚的缘由,迟至30年后的1987年才以《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书名得以完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宏观视野、史诗般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在蒙古草原上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茫茫的草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小说已经结稿,与我相交三十六年之久的那些人物,从此将不会在我的笔下重逢!我独自仰望夜空,心中充满莫名的惆怅。”在此前后,玛拉沁夫创作出版了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第一道曙光》《爱,夏夜里燃烧》,对草原的热爱,对草原上人与事的迷恋,让玛拉沁夫心中的牵挂和感动始终与草原紧紧相连。
“我写了一辈子草原,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我一直坚守自己的本位。草原养育了我、培养我长大,给了我一切,我将一生写草原文学。我是中国草原小说始作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我对中国文学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我走了一条开创中国草原文学之路,在我之前,在中国没有人用自己整个一生时间来写草原生活的。”
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茫茫的草原》,从青年步入老年,一个作家坚守着中国草原文学的点点滴滴,从而也成就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代传奇。玛拉沁夫说:“让中国‘草原文学’繁茂起来、成熟起来,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血乃至生命去浇注。”
民族心:两次上书建诤言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然是多民族的。”
1980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会步步落后。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很难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
作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颇为率直。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状况其实有着自己的看法。
1955年初,玛拉沁夫致信中国作家协会三位领导同志茅盾、周扬和丁玲。以“上书”的形式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他在信中写道:作家协会“忽视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然是多民族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在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上有一条讨论国内各民族文学状况的议程;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作家协会(以及原文协)对解放前或解放后国内各民族文学工作情况作过比较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和写过指导性的文字。”
写这封信时,玛拉沁夫未满25岁,他无私无畏,相信自己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两个月后,玛拉沁夫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复信。他打开信读到的第一句话是——“玛拉沁夫同志:你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在作家协会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主席团认为,你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复信中,作协对如何改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
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堂堂正正、再不容忽视地永远绽放在中国主流文学大花园之中。
十年“文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国文坛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挣脱出来,正在新的春天来临之际争奇斗艳。但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呢,用玛拉沁夫的话来说依旧是“一片沉寂”。此时内地的文学已经复苏,但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无心再从事文学,有些还戴着各种政治帽子。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会步步落后。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很难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
怀此初衷,1980年1月,玛拉沁夫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希望“中央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有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中宣部领导收到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国作协党组,并在信上做出批示,批示的内容十分具体:“我们确应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比如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比如创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等等”。
1980年5月,召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开会,讨论并经中国作协批准做出决定,这其中就有“于1980年7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1981年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立即创办民族文学期刊”“在文学讲习所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等内容。
同年8月,玛拉沁夫被调往北京主持筹办《民族文学》杂志,随后担任《民族文学》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1981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年年底,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每三年一届的少数民族文学奖评选延续至今,到2014年该奖已经举行了十届,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最高奖。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上书”之举,看到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作家已有万人之众,玛拉沁夫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一次国际文学会议上说:“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
一生谊:往事悠悠永难忘
“我所有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我的潜力的发掘、开发和发展,都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机遇。我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一个蒙古族少年在文学道路上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我感到非常荣幸。”
玛拉沁夫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他的一生与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与变迁紧紧相连,窥探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玛拉沁夫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视角。他是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的第一期学员;他参加过1956年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参加过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他从1989年至1995年担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书记处常务书记达六年之久;2014年他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回忆起这一件件、一桩桩文坛往事,玛拉沁夫十分感慨:“我所有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我的潜力的发掘、开发和发展,都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机遇。我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一个蒙古族少年在文学道路上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我感到非常荣幸。”
1952年,已在京完成《草原上的人们》电影剧本创作的玛拉沁夫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同志亲自担任他的文学辅导员(导师)。在这里讲学的人可谓大师云集,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艾青、赵树理等都曾在此讲课,玛拉沁夫称他们都是自己的“恩师”。
周恩来总理对玛拉沁夫的关心则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全国第一届青年作家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来到驻地看望大家,当总理得知有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参会时提出和他单独谈一谈。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玛拉沁夫依然十分幸福。总理说:“你学会汉语很好啊,我历来主张少数民族同志要学会汉语,不但可以与汉族进行交流,而且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交流,甚至可以进行国际交流,所以我主张少数民族同志要学会、学好汉语汉文。”总理话锋一转,提高声音接着说,“同时,我周恩来也一再说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学会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便于交流,更重要的是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各民族之间要相互尊重,只有互相尊重,才能真正团结,团结搞好了才能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国家。”
周恩来总理和玛拉沁夫谈了一个多小时,玛拉沁夫也由开始的紧张逐渐放松。周总理对玛拉沁夫创作和生活的关心让他每忆及此,都感动不已。
2014年,玛拉沁夫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谈到参会时的情景和总书记的讲话,玛拉沁夫依旧难掩心中的兴奋与激动。
“这么重要的会议,只开了半天时间,开会中间完全没有以往会议的过场和客套,如此简约、亲切,首先就表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平民化作风。”谈及此,玛拉沁夫感受强烈,“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不只是守住底线,而是应该达到高线和上线。文艺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不能在文化垃圾上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更不能在文艺雾霾中进行文化长征。”
玛拉沁夫在参加完文艺工作座谈会后谢绝了很多采访,他觉得自己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地思考,不要兴奋以后一阵风似的又过去了。
15岁参加革命,22岁成名于文坛,59岁担任中国作协领导职务,玛拉沁夫始终在文学事业中不断耕耘、不忘初衷。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玛拉沁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对自己说:“封门封嘴不封笔,写人写神不写鬼。”
玛拉沁夫正在撰写文学回忆录,回首人生,感慨良多,他说:“我参加工作已70年,凭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走到今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报培育我的党,共和国和蒙古草原!”玛拉沁夫依然满怀童心,曾经赋小诗以自娱:“莫悲落花白头翁,曾是红颜美少年”,说着他仰面大笑起来。
青春已逝,岁月风霜染白了这位八十五岁老人的双鬓,但是作为一个强者,玛拉沁夫依旧葆有一颗青春的心,美丽的梦,他说:“我已老矣,冲锋陷阵的重任,恐难完成,但我坚信在整体气场强盛的年月,我们中国作家终会有一天,站在文学高峰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的真善美!”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记者 雷晓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