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顾颉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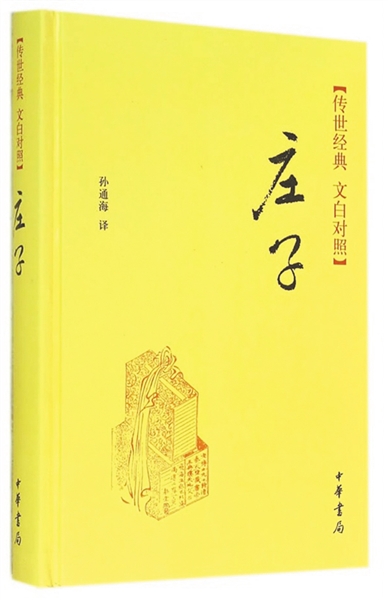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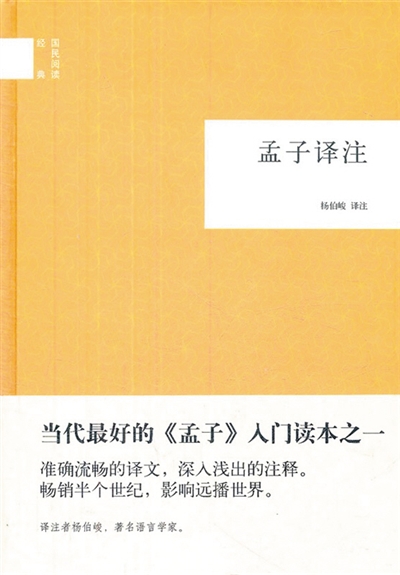

二十多年来,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知识的碎片化和人们对碎片知识的迷恋,认真读书的越来越少,引起许多有识者的忧虑。于是,发达国家提倡的“慢生活”包括“慢读书”意识传入中国。其实,中国传统的读书就像古代生活一样,节奏是很慢的,这一点从教育的起始就养成了。
一
明清两代,小孩初进私塾,拜完了孔圣人和老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第一册课本(一般是《百家姓》)请老师“号书”(标明下次号书之前应该背诵的段落,如从“赵钱孙李”背到“金魏陶姜”32字),从入学开始就是要背书,学过的经典都要背下来,这还不“慢”吗?那时所谓的“读书”不是默默地看,都要大声读出来。明代太监刘若愚在《明宫史》记载当时小太监在宫中入学读书(明代太监必须读书,清代则仅许其识字而已)情景:
每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生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
这种学习方式从教“几个小小蒙童”的私塾,到最高学府——庶常馆都如此这般。“庶常馆”是士人通过了最高考试中了进士之后,择进士中的杰出者为“庶吉士”(类似今日的博士生)到这里再读三年。清末进士恽毓鼎在日记中记录他在庶常馆入学的情景:
教习(老师)升公案上任,起行交拜礼,相向三揖。庶常等(众进士)行一跪四叩礼,后二叩赞礼者唱免,礼毕各退。顺甲第(按照进士考试的名次)进号书。十人一班,各执《大学》一本或《书经》、进至教习前,教习以朱笔标‘六月初四日’五字于简端,乃退,以次号书毕,教习行,庶常皆恭送于二门外,各乘车而返。“(《澄斋日记》)
记载很生动,这些至少也都二三十岁的饱学之士、像小学生一样抱着小学课本,要“教习”(年龄未必长于学生)给他们号上背诵的段落。这一方面体现了尊师,又表示对经典的尊重。
那时人们读书叫做“点”书,这种称呼直到比我们大一两辈老先生仍然保留着,读《顾颉刚日记》常见“点”某书“一过”,也就是读某书一遍。最初我以为这是他读没有断句的线装本,随读随点,读完了也断句了,下回再读就省事了。后来发现有标点的书也这样写,如点《毛选》中某篇,甚至读《人民日报》读文件也说“点”,看来“点”就是读。过去在坊肆中买的线装书大多没标点,确实要随读随点,这还不是慢读吗?
那时的知识人对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要背诵,要融化在血液中;对一般非经典书籍,读的时候也很认真、仔细。因此老一辈的学人的基础知识都很牢靠。读王念孙(清乾嘉时学者)的《读书杂志》、闻一多的《古典新义》,从中可见这些学人在考证一个字、一个词时,几乎穷尽古籍中关于这个字、词所有资料,而且都是顺手拈来,十分随意,仿佛现今用的数据库检索,老辈学者对古籍熟悉,由此可见。这都是“慢读”功夫的显现。
另外,传统的读书习惯中还有抄书一项。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都是手抄的,有文化的穷孩子还以抄书为业。李商隐年少丧父,十六岁到洛阳“赁书”(为人抄书)贴补家用。即使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也很难得,爱书人、读书人借抄书籍是很普遍的事,这样既熟悉了书籍,又获得了书籍。顾炎武曾以自己为例说,他从十一岁开始抄读《资治通鉴》,经历了三年的熟读和抄写后,他有了三本九百万字的《资治通鉴》,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熟读的一本。近代印刷工业传入中国,书籍唾手可得,许多老人仍保留着抄书的习惯,《鲁迅日记》《顾颉刚日记》中都有抄书的记载。顾先生直到七八十岁时在报刊上看到于他有用的文章还是抄下来保存、备忘。
不过那时书籍少,流传到现在的古籍不过十几万种,刨去辗转相抄的,大约不过五万种。人们都是“术业有专攻”不必把这几万种书都读完了(不过清末民初,“诗界革命”中三大诗人之一的夏曾佑先生对向他辞行到海外读书的陈寅恪先生说,你们懂外语真好,我不懂外语,中国书都读完了,没书读了),所以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慢读、反复读、边读边思考。从我个人经历看也是这样。自1949年建政以来到“文革”的十七年间出版的文史古籍和研究著作,我不敢说都看过,但敢说大多翻过,至今心里还有个数,因为那些年出版的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种数有限,稍上点心就有记忆。现在不行了,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书籍的出版也如江河汹涌,隔一两个月我就会到院图书馆新书架上浏览一下,真是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吸引我的太多。有的很沉的书背回家来,别说“慢读”就是快读(或借用网上一个词“闪”读)三个月内(借书期限)也读不完,有的还没读,就又去还,真是为书所累。台湾“联经”版的《顾颉刚日记》十二本,每本都有二斤多,因为想细读一下,做点笔记,断断续续读了有两年多,背来背去,四五趟,其辛苦自知。
二
传统中的“慢读书”根源于对读书目的的认知。古人认为读书关系着人格的养成,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都应该在读书中获到解决。荀子在《劝学篇》中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儒家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像尧舜一样的人格,荀子认为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就要终身读书学习,这是成为尧舜的必由之路。因此读书不能仅仅“出乎口,入乎耳”,而是要在“口”“心”之间,反复往来: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荀子认为“出乎口,入乎耳”的读书不能到达人的心灵的深处;只有深入心灵的读书才能化为人生的实践,支配人的一生。
也许荀子说得有些玄虚,今人流沙河先生在答《南都周刊》记者问,谈自己读书体会时说:
《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这个“人格的改变”就是指读书可以“移性”,把人的品德气质提高起来: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他很好地说明了慢读书与人格养成的关系,也批评了当前语文教育的狭隘与卑琐。他提出的“文化人格”值得关注。
我年轻时候也背过一些古文诗词,现在早锻炼的时候也常常复习。我曾对孩子说,一定要背书,有些书你只有记在心里,才跟你的人格融为一体,对你产生影响。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唯有读书可能改变,因为你脑子里坐着一个时刻指导你的人。设想一下如果你脑子里有位司马迁或杜甫坐在那里,对你的行为思想会不会有些约束。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文化人格的权利,不一定完全与流沙河先生相同,如果你敬仰鲁迅、胡适想法效他们,也不应该停留在某些概念与话语上,应该熟读他们的作品,体会其人生处境掌握他们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也不是草草读几遍鲁、胡的名篇所能解决的。

杜诗更需要反复吟咏才能深入领会忠爱精神和超越意识。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历来讲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在述”。其实感动人的从“杜陵有布衣”开始到“放歌颇愁绝”这三十二句。杜甫在这段反复陈述出仕与归隐的矛盾,是儒家的忠爱精神启发了他对社会的责任心,反复吟咏才能领会到诗人的苦心,从中获得一份感动。
——王学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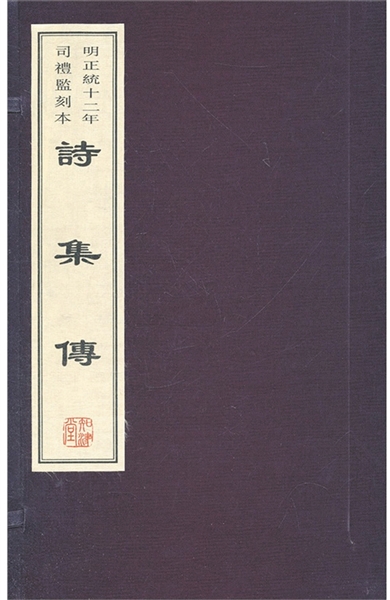


《坎坷半生唯嗜书》 王学泰 商务印书馆 2011年6月 定价:34.00
三
我虽是学文学的,但对历史更感兴趣,因为大多文字资料(包括文学作品)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章太炎先生的“六经皆史”说是有道理的。其实民国时期国文教育是文史哲经不分家的。
因为喜欢历史,老辈学者告诉我,喜欢文史一定要从起源头开始,具体说就是先秦两汉。熟悉这个阶段的作品,才能理解其后的各类作品。因此,我在读这个阶段作品时是反复读、慢读、细读,最好是背熟。
从初中起,我开始背书,最初是背唐诗宋词,上高中就有意识地熟读和背诵先秦两汉作品了,熟读的如《论语》《诗经》《左传》《战国策》《孟子》《庄子》《古文观止》上册(所选都是唐代以前的作品)等,背诵艰深难懂的。如《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与“风诗”中《七月》《东山》,楚辞中的《离骚》《九歌》《大招》《招魂》《庄子》中的《齐物论》《人间世》等。高中时正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红专辩论”,读书简直成为一种罪过,动不动就会飞来一顶“白专”的帽子,更不用说读“死人”、洋人书了。由于个人癖好,我还是坚持背书。我在六十五中读高中,家在菜市口一带,坐九路无轨到校,大约需半小时,我就利用这段时间背。那时几乎不怎么上课,作业也少,下学回家不带书包。我衣兜里老揣着一本马茂元的《楚辞选》,或朱熹的《诗集传》,在车上背。后来还背过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陆机的《文赋》和《文心雕龙》中一些篇章。其实,当时是半懂不懂的,对于作品的意义更是茫然,然而使我终身受益。我读大学时,文选课和中国文学史就没怎么用力,而这些课文对许多同学来说是难点。后来我从事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因为材料熟,很容易激发联想。
例如前几年写《〈论语〉在中国文化史地位演变》,再读《论语》就有一些新发现。例如《论语》编辑似乎很随意,然而开篇的两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细一思考,我觉得它们反映当时两个重大的社会动向。一,本来是“学在官府”的,能够进入学校学习的大多是贵族;到了孔子时代则可以说“学入民间”,平民子弟本来是没有学习机会的,更不用说“学”而后再“习”了,这里孔子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努力学习,说明读书学习已经为广大平民所知,有志于学习的平民子弟也有可能踏入校门,通过读书学习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了!二,西周本是垂直统治专权社会。其社会等级是周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奴隶;这是一个流动性很小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位置,一般只与上下有关,人们之间没有横向往来,所以“大夫无境外之交”,人们基本上也没有朋友关系,(几十年前有的学者把“朋友”解释成有血缘联系的宗亲),现在人们有了横向关系,有朋友从远方来,这说明,原来的垂直控制正在解体,周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也在一天天崩溃。
又如在考查《论语》的形成时,读班固《汉书·艺文志》,觉得其中记载值得注意,如在记录传世《论语》时说“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登载这“十二家”时,除了《论语》不同传本(如《鲁论》二十卷《齐论》二十二卷)和论语一些注本外还有下面一些似乎与《论语》并无直接关系的书籍: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议奏》是《石渠奏议》的一种,是讨论《论语》的专集。西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召集名儒在未央宫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议奏主要是讨论五经的,但其中也有关于《论语》的十八篇。其他如《孔子家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家属言行的,《孔子三朝记》是记载孔子朝见鲁哀公的,《孔子徒人图法》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图像的。可见汉代士人把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记载都视为《论语》,那么我们对“论语”书名真实含义就要做些认真的考察了。
《汉书·艺文志》解释《论语》时这样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定义为后世所接受,可是验之以班固自己的记载,这个定义又似乎不够准确。
“论”的繁体是論,論古代也写作“侖”,侖字上是“亼”(音集,意义也为“集”),下面是个“册”字,“論”的原始意义就是把一些竹简拼合在一起;虽然言、语、话、说现在都可解释为话语,但三者还是有区别的,“语”更多有告诉之意。如《庄子》中“夏虫不可语冰”,这个“语”可直译为“与它谈论”,意译也是告诉它。《论语》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如果自上而下地“告诉”往往含有教诲之意。孔子是做教师的,《论语》在记录孔子的言行时往往是弟子们的回忆,这样用到“语”这个词汇更增加教导的色彩。孔子曾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是教育学上的一个原则,是孔子一个发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这是孔子赞美颜回这个好学生,接受教育时而不怠惰。这个“语”就可直译为教诲、教育。因此“论”“语”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其本意应当是:把孔子对弟子的教诲之语编辑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孔子言行录”。
孔子是第一位把学问传播于民间的人,先秦学派纷纭,绝大多数都从孔子那里吸取不少智慧和学养。孔子生前就被视为“圣人”,吴国使者专门派使者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答复之后使者很满意,说了句“善哉圣人”。因此,孔子作为“轴心时代”华夏文化的开山者,又是“于事无不通”的圣人,自然其言行受到各个学派和学人的重视,他的语录到处流传,甚至编辑起来作为学习“六经”(华夏元典,各学派都用它做基本教材)的参考。像郭店楚简、“上博”竹简中的许多难以归类的散简中的文字,其内容风格很像孔子语录,说不定也就是“论语”,只是其编者与流行本不同罢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汉书·艺文志》的“论语类”中收录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孔子徒人图法》也就不奇怪了。
我不是像胡适先生那样“有考据癖”的人,平常阅读也很糙,但读熟了的书,再读时往往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四
读书是一种美的享受,回忆起少年时期为读一本有趣的书,或读一本能够启人心智的书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情景,如在目前;现在老了,不敢全身心投入地读书了,但现在更能体会慢节奏的读书也是别有一番趣味的,这样可得涵咏之美。宋代大儒陆九渊就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
优秀的文史作品都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不像现在历史多品大多质木无文。《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很多分析都在强调“郑伯”为人阴险,忽略了其中有人情味的一面;该篇的最后一段:“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郑伯是长子,老妈爱少子,处处偏疼小儿子共叔段,导致了共叔段坐大闹事,给国家带来麻烦,此时说出了与老母一刀两断的绝情之语。可是毕竟母子情亲,事情过去之后,心上留下拂拭不去的阴影。此时潁考叔介入了,郑伯一句“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他的内心活动暴露在读者面前。
原始的儒家思想更多是感情哲学。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时感受到感情的冲击。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那么在于什么呢?孔子认为在于仁心俱足,在于敬畏和真诚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衷于外在的规范(只对颜回这样类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讲一点规范——“克己复礼”),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因此可以说“仁”的内涵就是“爱”,就是对他人倾注更多的关切。这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可以说它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孔子其他一些关于“仁”的论述(确切点应该叫“述说”,因为其中没有什么“论”),都是在述说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因此体会儒家思想不在于说教,而在于“涵咏”。最能弘扬儒家思想、把儒家意识注射到人体内的是诗人,而不是语言无味贩卖高头讲章的腐儒。
在诗人中,最有原始儒家精神的是杜甫,他内心之中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甚至超越了孔孟。
杜诗更需要反复吟咏才能深入领会忠爱精神和超越意识。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历来讲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在述”。其实感动人的从“杜陵有布衣”开始到“放歌颇愁绝”这三十二句。杜甫在这段反复陈述出仕与归隐的矛盾,是儒家的忠爱精神启发了他对社会的责任心,反复吟咏才能领会到诗人的苦心,从中获得一份感动。
五
在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讲“慢读”真是有些奢侈,然而还要提倡“慢读”。刚刚朋友传过来一片网文——《中断时代:碎片化造成现代人智商下降》。这篇虽然是讲手机、电话、邮件造成了时间的中断,使得人们很少有整段时间思考问题,整天忙着看电脑、手机,造成时间的碎片化。其实,人们热衷于从电脑的搜索和手机的微信中获取知识,其所得到的也是极其肤浅的信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还是沉下心来的去阅读能为人生和你从事的工作有用的基础知识。探求真理式的阅读,那更要慢,在慢中才能有深入的举一反三的思考。
该文还说:“文字表达则需要读者在头脑中将文字转换成画面,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记忆、情感去破解文字的密码,它需要耐心品味,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要停下来想一想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一味地‘快’”,这些意见值得我们思考。
(王学泰)

